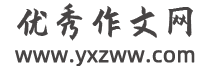凄风。苦雨。昏天。黑地。
外婆家熟悉的堂屋俨然成为了一个被白纱白菊笼盖的礼堂。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赤红的沙砖地上,静静地安放着一具红木棺材,纸钱的余烬和闪烁的烛火一唱一和,外公就在那儿安详地睡着。
这场葬礼的一切,都被一个被家乡的人们称为“三表姐”的人主持得井井有条。她是我们那儿办这种事情的权威,毛躁的短发像爱因斯坦,向周围放射着令人们惊叹的能量。听别人说,她最擅长的是哭丧。
在道士们的吹吹打打中,七天过去,外公的遗体就要送去火化了。力夫们在堂屋里围着棺材,“嗒嗒嗒”地捶打着棺材上的木钉,紧接着便把棺材抬出了堂屋。
外婆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哭了,浑浊的眼球里溢出了清澈的泪滴,沙哑的声线在堂屋里被无限地拉长。三表姐也哭了:她用一条在陪礼袋里顺来的一条全新的毛巾,半捂住狰狞的脸,不住地发出“呜啊呜啊”的号叫,臃肿的身体佝偻成了一个浑圆的球,就那么立在地上。
“哎,你看这三表姐哭丧真有一套,一定赚得不少钱!”有人说。
听到这,三表姐哭得更卖力了,扭曲蜿蜒的号叫中竟透出几分得意与炫耀。
送行的队伍出门了。漫天喧闹的锣鼓声、号叫声、说笑声和外婆微弱的哭声在马路上不停地引来路人的目光。外婆的脸肿胀着,像个浸了猪血的馒头,过度的伤心使她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意识,只知道不住地哭泣。我扶着外婆在队伍的中间踉踉跄跄地走着。
“妈,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无谓的东西?”表哥在一旁,无意中道出了我的心声。可他话还没说到一半,小姨便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你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只有这样你外公才能在那边过的好。”说完便殷勤地给哭的很卖力的三表姐递过去了一瓶矿泉水。
队伍的末尾,三表姐的徒弟们抛洒着纸钱,米白色的纸钱像雪片一样在空气中无力地挣扎,然而总是飘不到人们想让它们去的那另一个世界里去,最后落到了大路旁的臭涌里,被里头翡翠一般、浓稠的液体裹挟而去。
我扶着接近昏厥的外婆落到了队伍的末尾,我看着他们,竟像看着一出闹剧。
一切终于结束了,回到了外婆家,是死一般的沉寂。为了安置外公的棺材而腾出的大片空地也变得寂寞。赤红的沙砖地上流满了浑浊的烛泪,洒满了脆弱的纸灰,曾摆过棺材的那一小方地是最洁净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些什么。
我怅然看着堂屋里的一切,只见一支红烛默默立在墙角审视着这一切。那摇曳的烛火像是看懂了什么,摇了摇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