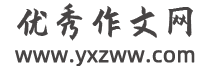在初中以前,猫这种动物于我而言还有点陌生,直到那个小小的它来到我家时,我与猫之间的联系才开始加强……
起初我们待它如婴儿一般,因为它那时是多么的弱小,一个A5纸做的小盒子都能轻而易举的装下它。但听母亲说它刚生下来便遭遇了不测,所以它看起来总是很胆小,警觉,一碰它便会伸出尖锐但未长全的爪子。
在我们的悉心呵护下,它也长大了。黑白的毛发更衬托出了它的高冷,黑毛隐约显出的蟒蛇纹也恰似它的性格一般神秘古怪。它依旧十分警觉,还不懂分寸,和人玩耍,从不收爪子,为此我的手上多了几道爪痕,它的身上也挨了不少的拳头。
毕竟我身为它的主人,它对我也必有依恋之情。上海的冬天虽不比北京温度低,但却湿冷冷的,晚上纯靠电热毯和那条厚厚的羊毛毯。猫自然也不傻,总在我钻在被窝里看电视时,悄悄爬上床,静静地团坐在羊毛毯上,两只肉爪揣在胸前,闭上眼睛,一脸安逸。“猫起被余温”每晚当它离开我时,我总用手感受着那余温的消逝。
每晚写作业时,不论我写到多晚,有时甚至连父亲都已上床时,它也会坐在桌角一直陪着我,还是两只肉爪揣在胸前,闭上眼睛,一脸安逸。
搬到北京时,我硬带着它过来了,但我不知道它可能永远也适应不了北京。来北京后我忙了许多,不止我,所有人都如此。于是对它便少了许多关注。渐渐地,它开始变得神经兮兮,在无数次我忘给它盛饭倒水后,它开始每晚嚎叫,在床上撒尿。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看到它被拴在椅子背上。当我靠近它时,它疯狂地扑向我,用慌张,乞求的眼神望着我,随即又被绳子勒了回去。吃饭前,母亲很严肃的坐在餐桌前,不动筷子和我说:“我和你爸决定了,把它放到小区里。”那时我不能接受,我开始哭着央求他们,在等一会儿再过一段时间,但这并没有。第二天晚上,母亲把它放下去时问我:“你要去吗?”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看到它离我而去,没等母亲走多久,我便后悔了,因为我想再见它最后一面。我冲下楼去,狂奔,感受眼泪从眼角流向鬓角,感受路灯被眼泪遮住,到它身边,抱住,最后看了它一眼,把它圆圆的眼,黑白的猫,永远映在我的脑海里,狠狠亲了它一口,把它给母亲,再一口气跑回家。我知道这次的离开不同于“猫起被余温”,因为余温已不会再有。我想到了失去,但不是失去一个人,一段往事,而是一个毛茸茸,无声的陪伴。
“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们并非灾祸。每天都失去一样东西,接受失去房门钥匙的慌张,接受蹉跎而逝的光阴……——毕肖普”。
但我很难想象,它真的会离开我。我曾经还计算着它的年龄,盼它能伴我一直到大学。失去并非灾祸,因为失去了它,才让我发现自己是有多么不负责;因为失去了它,我才会做每件事时,都认真去做。
接受失去,接受失去带来的悲伤现实,也接受失去带来的教训,接受失去带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