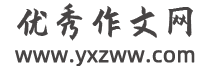我垂下眼,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副画面:那是一个头发少的可怜的头顶,能清楚地看见下面暗黄的头皮。一缕缕极细的发丝夹杂着些许银色,按着被梳子梳出的纹路,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然后再由一个简洁的黑色橡皮筋,整齐的扎好。发梢轻轻地耷拉在背后,温柔的服帖着……
是整齐的,却不难看出沧桑。
已经很晚了,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刚刚到家。却发现母亲半倚着沙发缓缓转醒,想必是被我响亮的关门声吵醒的。我不以为然,心不在焉地叫了声:“妈……”随即进厕洗漱……简单洗漱后,母亲还在原位:“过来。”她说。手里拿着“紧箍儿”。欸,我无奈,又要念“紧箍咒”了,我不耐地想着,却不得不走过去,一脸不情愿。
此时的母亲正蹲在地上,埋首在为我绑腿——是的,我有一双不太好看的O形腿,母亲显然比我更焦急:多好的一姑娘,这腿咋这样呢?一定得给它纠正过来!不知在哪儿看到的,她买了两条“绑带”,每晚都给我绑上。我便以这个视角,看到了她的头顶。
也没有了不耐,我盯着她这样一片头顶,不免有些辛酸。据说她原来有一头乌黑油亮的直发,那一直是她的骄傲,而却在生完我后,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变成了现在这样,想到这里,我又有点愧疚,落在那头发上的目光,也多了份怜惜。
“嘿!”她一个用力,把两个粘扣搭在了一块儿。我一个不稳,双手紧紧扶住了她的双肩,隔着厚实的羽绒服,我清晰地感受到她并不厚实的肩膀。她身体呛呛向后倒了下,随后又稳稳定住,继续为我绑腿。手还搭在她孱弱的肩上,看着她头顶少得可怜的发丝,从心底涌上一股不知名的酸涩,有一瞬间竟像着了魔症般,仿佛我是母亲,想伸手抚上她的头,像往常她抚摸我一样。不过手还没抬起就已放下,僵在身体旁,不知所措。还是望着那同样的头顶,眼里干得生疼……
我半开玩笑道:“老娘啊,还是你好。”她片刻不停手上的动作,抿紧嘴唇再完成一个搭扣后才缓缓说:“是哦,只有你老娘才不会嫌弃你,为你做这种事哦。”我咧嘴笑得极开心,眼里,却深深刻进了那头头发。
那些银丝,是对我满满的操劳,那凋零的发,是数不尽操碎的心……
我就一直盯着这幅画面,突然停止了动作,就想这么一直看下去,仿佛这样,我才能少一些愧疚。而母亲却起了身,长呼了一口气,她穿着高跟鞋,我再难看到那幅画面,却意外觉悟:母亲是脆弱的。她把自己的脆弱隐藏起来,隐藏的技术其实不怎么高明,就像那一头头发,明明已经露在最外面,我却从未发现。我想,不是她善于隐藏,而是我从未去寻找。我总以为母亲很强大,无所不能,却从没去关注她的不易。
我的母亲,总是用像绑腿一样简单粗暴的方式一次次纠正我的错误,而我,虽然痛,却总算被调教回来了,可是那被强迫的怨气,却从未消散过。直到今天,直到看到那幅画面,也不需要再多的言语,便全通了。可是无法改变的是她那枯败了的发……
那幅画面,从此在脑海中定格,几次惯性地想要遗忘,都被我生生地压下来:不能忘!
也许现在还无法做到煽情地拥住母亲的发,但这幅定格的画面,我要牢牢地烙在脑子里。我告诉自己: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