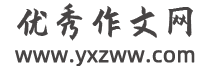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打发走了一大波人,店里顿时清净了。邵大姐甜甜地亲了口刚过一岁的小儿子,小家伙咯咯地笑起来。似乎知道妈妈得空了,便用他那圆乎乎肉嘟嘟的大脑袋使劲地在邵大姐怀里蹭过来蹭过去。又逗了下小家伙,邵大姐娴熟地掀起衣裳给他喂奶。
樊姐抚摸着膝盖拉了个凳子在可以晒到太阳的玻璃门前坐下,“店里太阴了,腿都冻疼了!”她笑着对我说,“是啊!”我草草地回了句。不一会儿,竟感觉一股凉气从裤脚“嗖嗖”地贯彻全身,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于是,我也拉了个凳子和樊姐面对面坐着,“我们这样多像看大门的啊!”樊姐听了浅浅地笑了下并不搭话,我便没有再言语,百无聊赖地望向了门外。
阳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隐约描摹出大门的形状,也勾勒出我和樊姐靠着的椅子和身体的轮廓。门外大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前四后八带动灰尘家族的千军万马,它们高昂着头颅目送着车辆的远去,像是送别自己将要远行的儿女。大路对面梧桐树下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老头老太太,有个老太太正眯起眼睛给自己的小孙女梳头发呢。我摸了摸头发,想起小时候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被妈拉起来梳起的小辫子。那时候走在上学的路上总是被人夸奖,“这谁家的姑娘俩小辫真漂亮!”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啊。
一个人影从眼前晃过,将我拉回到现实当中。门被一个中年妇女推开,身子探了进来,等紧随其后的中年男子进来了之后,她才缓缓地松开门把手。我起身悄悄伸了个懒腰,樊姐也站了起来,给他们介绍各类商品。后来因为是要锅还是要被子的问题他们竟起了争执,声音不大,却还是让我们有些为难。
中年男子看了看我们,回头对中年妇女说:“你自己挑吧,想拿啥拿啥。”说完拿出一根烟出了店门,侧过店面点了烟,自顾自地抽了起来。“你看这人!”中年妇女一边反复查看选中的被子一边念叨了句。过了一会儿,中年男子进来了,“挑好了没,要不就拿被子吧!”显然他妥协了。我们赶紧接腔,“那包起来了?”“好!”他们齐声说。我们三个相视而笑,既欢喜于他们的默契,又为卖出商品而感到高兴。送走了他们,已经快要看不到太阳的影子,我们随意的收拾了下,锁上拉闸门,互相打了招呼,邵大姐和樊姐结伴而行,我就骑上我的“小毛驴”驶向了回家的方向。
一路上微风扫着耳稍,柳絮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蹬着自行车的样子被夕阳拉的老长老长。日子这样循规蹈矩的过着,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换了一座城市,重新走进一个圈子,同样的一个人,却可以造就不同的模样。身边的人行色匆匆,却似乎总是少了我一个。
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样想着孤独感油然而生。曾经那个含苞待放的年龄,不甘平凡的我像大多女孩一样奢望过能够拥有一段轰轰烈烈地爱情。可是年轻不愿等待,它经不起所谓的轰轰烈烈,当我们懂得了一切最终都要归于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像那个中年妇女一样愿意为丈夫开一扇门,也会像那个中年男子一样面对争执选择妥协。那不是软弱,那不是怯懦,那是为了家庭情愿为彼此让出的一小步,那是平凡琐事里彰显出的无微不至,那也许才是真正渗透于点滴生活中的爱吧!
我猛蹬了几下脚踏,路边的常青树哗哗地向身后退去。很快就可以到家了,圈圈一定早已等待在大门口,打开门妈亲手熬的玉米糁一定散发着诱人的香馋的我口水直流。
晚上和妈到外边溜达了一圈,圈圈摇着尾巴在前面带路,一街两行的霓虹灯闪烁不停。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让我成长的地方,处处充满爱,而我还在到处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