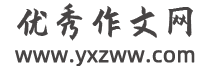食前方丈,家宴至美。
天边还泛着一抹红,窗边却已腾起一片轻烟,袅袅之中,满是团聚的幸福。
外婆站在大灶前,一只炒锅盈握在手,一翻一炒,那菜肴便乖乖被抛起,又精准落入锅中,火苗向上蹭蹭窜着,映出外婆专注的神情,尽显“厨神”之姿。
在外婆的吩咐之下,我的工作是切菜,虽是件不算太难的任务,与外婆相比却依旧弗如远矣。静下心来,我小心翼翼的握住刀柄,对准冬笋的纹路,“咯嚓”一声,冬笋一分为二,刚想为自己小小的成功沾沾自喜,不料被外婆一把夺去了刀具:“这样切太慢啦,来,我教你。”说罢便握住我的手,让刀尖对准其中一条纹路,突然,手腕一发力,手起刀落,眼前便只剩下笋片翻飞了,像那快刀斩乱麻般,一只完整的竹笋,眨眼间成了一片片轻薄透亮的竹笋片了。惊诧之时,外婆早已把它们倒进锅里,和着热油烫过的肉片翻炒起来,不久,一道嗤嗤冒油的竹笋炒肉片便端上了桌。
窗外只剩下一片漆黑,家家户户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称着若隐若现的月光,撩人心弦。外婆常说,做宴席讲究五个字:质,色,香,味,器,缺一不可。“器”是外婆搬出的一口大砂锅,置于灶上。“质”是她命我提来的那只她特地从乡下带来的老母鸡,拔毛,破肚,切去头尾,再一碗清水配着枸杞,黄芪,当归等食材一齐倒入锅中,小火慢煮。“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做一方宴”我们家祖传的正是这竹笋土鸡汤。
火舌从灶口冒出来,外婆的影子贴上后墙,忽大忽小,斑驳摇曳。罡风缠绕窗棂发出呜咽,屋里的温度重新升起来,热量向着寒冷四散突围。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外婆撮起嘴,吹去锅盖上的蒸汽。揭开锅盖,如同揭开一个谜底。鸡汤怎么样了?锅里是那黄橙橙的还在不断上下翻涌的浓汤。用勺子捞去上层的鸡油,外婆撒下大把翠绿的葱丝,锅盖合上再合上时,她用毛巾环绕住锅与盖的缝隙,让蒸汽闷在锅里,但仍挡不住渗出异香。
窗外鞭炮声响起之时,鸡汤隆重上桌了,异香氤氲,嫩香腆润,这是浓浓的亲情,是家的味道!
看着一家人围着饭桌大快朵颐,外婆终于长舒一口气,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脸上的皱纹又深了一点,这是岁月磨出来的痕迹。
许多年后的家宴外婆是否还能做出美味的鸡汤?将来的日子里外婆的刀功是否还是这样雷厉?若是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了”但现在看着外婆劳累的背影,我犹豫了。
鸡汤是祖传的,刀功也是祖传的,他们应当有人继承。要知道不论是批切削斩,还是煎炒烹炸,全靠代代传承,耳濡目染,才能制作出地方风味的菜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