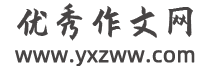七岁
放学后,我与父亲一起回家(父亲当时是民办教师)。时值春夏交替时节,发黄的小路被枝叶覆盖住了大半。碧绿的叶子间露出一点点阴森。我手持一根小棍子,在前面蹦蹦跳跳。
父亲则拎着我的书包在后面,微笑着说:“慢点儿,慢点儿。”
调皮捣蛋的我从不在乎父亲的话。
只管用自己手中的木棍狠狠的抽打路边的枝叶。被抽断的枝叶无赖地躺在路边。在路边显出被蹂躏的惨状。抽断了一些,还有一些,我就像战场上的将军绝不留下一个敌人一样,赶尽杀绝。
这时,父亲便催促:快点儿,天快黑了。不然,又要走黑路。
父亲任教的学校离家非常远。我们父子俩“跑夜路”是经常的事。常常是母亲做好了饭菜在等待我们回家。夜行赶路时,父亲便让我在后面,他在前面开路。让我跟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走。还不时回头叮嘱我“小心点儿”,后面的我此时一想到老人们平常讲的“鬼故事”,便胆颤心惊。但每每听到父亲的催促声,我便要加快速度。跳一下,打一下;打一下,跳一下。有一次,正当赶路时我突然听到身后有“吱吱”的叫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蛇正张着嘴向我爬来,我吓呆了,站在那里不动弹,大叫“爸爸,爸爸。”父亲闻声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蛇的尾巴,迅速在空中舞了几个回合,扔向草丛边。那一刻,我觉得父亲是英雄,好伟大,好伟大。
十四岁
这一年,我有幸考入县城中学。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父亲不知为什么再也不能教书了。父亲便夜以继日地看书,当起了乡下医生。
进入县城中学后,我斯斯文文,学得乖巧多了,再不像小学时一样撒野。
记得临近期末的时候,天气特别冷。虽然是农村少年,但还是经不起刺骨寒风的袭击,我患了严重感冒。
一天下午,父亲背了一大包药来看我。他头发零乱,进寝室时气喘吁吁。我猜想,父亲是下车后就直奔这里来的。几个月不见,我感觉父亲现在憔悴多了,原来挺直的脊梁或许因为生活的重压开始微倾。父亲给我输液时,我第一次认真读着父亲,他躬着背,手背如蚯蚓爬行时一样的静脉和起皱的皮肤,非常粗糙,前额深深的皱纹不知折叠着多少沧桑的故事。我再也忍不住了,紧紧地抱住了父亲,父亲也紧紧地抱住我,任泪水在父亲与我之间缓缓流淌。
今天
我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慢慢咀嚼着人世间最深沉的爱。
父亲把笔直的背给予了我,却承受着生活的鞭笞。
父亲把浓浓的黑发给予了我,却任凭白发落地、生根。
父亲把光明的日子给予了我,却享受黑夜的阴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