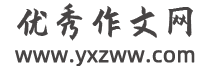窗外,风起。零落的扬花,轻舞,飞扬。低徊缠绵,如我抑郁的
心弦。五溪,东风不至;龙标,家音难寻。怎解心怀?不如归去,而畔杜鹃声声泣血,哀转久绝。夜已深,仰望苍穹,广茅的天空,一轮孤月高挂,冷寂无声。好友已去,我心如月。寂寞何堪!就将愁心托于冷月,把我这一缕绵绵的思念和愁绪捎去,万水千山,我心相伴,直到那最荒远的夜郎。
殇,扬州
我十六岁的时候,三月里的扬州正郁郁繁华。富贵温柔乡金粉清秋池。少年打马而过残阳古道,江南采莲的少女碧玉搔头落水中。祖父捻须微笑,在庭院弥散一地的山草药香味。
隋末,烽火乱世。我和我的做祖父住在淮桨影的扬州,守着一块九味堂的金字招牌。在漆黑的乌木台后,把褐色的当归和殷红的枸杞到进朱红的
陶罐。,一屋都是哀冷的香。
我最常保持的姿势是坐在窗户边,在一匹匹展开的丝绸上绣那些华美的牡丹。三色的丝线从丝绸的身体穿过去时有艳丽的破裂声。
于是牡丹一朵一朵,绝世的姚黄魏紫翩跹开放。
第二天清晨那些新鲜的牡丹会和朝阳一样高高挂起在城西三色坊中,笑容娇柔明媚。
我的手指从未碰过一株药草,尽管挂着九味堂唯一少主人的头街。
燕娘看见我祖父的的目光深邃不见边际。她说薄瑾,你的手为绣织而生,天上人间,于此盛极。别的东西,沾不得,否则就糟蹋了你这灵秀才气。
祖父在我的身边无奈地叹息。他再一次说,薄瑾,和我一起来分拣药草吧。而我一言不发,于是他只有长长地叹息气。眼神模糊而黯淡。
我听到大街上女孩子们的歌声,清澈纯净,像高高飞起有着漂亮容颜的纸鸢。可是我也听到了马蹄和弓箭的声音,炀帝的
头颅在江都落向了冰冷的大地,坍塌的城池被白骨埋葬,战马嘶鸣千里不绝。
繁花吐尽的扬州终于也开始恐慌,一地杨花覆在清冷的街巷石板上,像来不及化去的雪。
祖父往城中的街头巷尾贴告示。快马平剑的少年一字一句地把它念出来:本堂即日起封存疗伤圣药九转膏,所有刀伤剑伤。来历不明之伤一律不治。其余患者见伤给药,一次一贴。
祖父终于老了我悲哀地想。他拘楼的背影如此寂寞。他颤抖着手把一帖一帖的九转膏装进瓦木罐,封死,长埋地下。而这个夜晚真的显得太过漫长,好像即将持续一生一世,并且再也不会结束。
师父燕娘第一次没有来取我的织锦,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她才穿过冰冷的巷子,告诉我有人死了。
被惊恐的
人们围在中间的少年仰面朝天,已经冻结的眼珠像是死去的鸟。他是前一天骄傲地骑在马上一字一句念着我祖父告示的少年。我记得他曾经明亮如晨星的瞳孔。他被着剑离开,可是只有亡魂归来。
年轻的士兵茫然举起血花妖娆的剑,狼烟燃起在满目疮痍的古道。
燕娘在我的屋子,声音低沉而诡秘。她说,你可以救他的吧,你发现他的时候还剩最后一口气不是吗?
背对她,我看见祖父的肩膀微微地抽搐。燕娘的脸显露出莫名的凶狠:可是你胆小如鼠,惧怕卷入乱世纷争,引火自焚。
然后她转过头来看到一直沉默在们旁的我,轻轻地拉起我的手,她说,薄瑾,你冷吗?
窗外春色依旧,凄凄迷人,而我那么冷。
祖父的脸庞微微垂下来,上面有痛苦和挣扎的曲线。他说,孩子,不但你不相信,我连自己都不相信了,可是你要知道,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还没来得及再一次摇头,或者点头,鲜血就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溅落在我衣裙的牡丹上,汩汩流淌。血中的牡丹愈加的芬芳而诡异。
而我的祖父,他缓缓躺在了我的脚边,而面容清澈而疲惫。所有未完成的答案,就好像初春春色阳光下的雪丛脉脉化去,瞬间就毫无踪迹。
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死亡的无可奈何。想要说的话,没来得及给与的温情,在咽喉间铺天盖地的上涌。最后,却只能顺着整个空凉的呼吸道,落满失语的心脏。燕娘用一只手轻轻地遮住我的眼睛,可是我的眼睛却像突然有了透视的功能,我看见燕娘另一只手里的青瓷碗,里面是祖父喝剩下的半盏茶,茶渍乌黑似古井。我突然就觉得手脚冰凉。
祖父下葬的那天是扬州最苍凉的一个阴天,稀疏散落的人群带着庄严的悲伤,头磕在坚硬的石板上发出寒冷的铿锵。我远远的看见燕娘,像一只孤独的侯鸟。在所有断裂的翅膀之歌里,我的祖父,他说。薄瑾,你要好好地生活,直到一切结束了为止。
我说,好。所以我开始一个人生活。燕娘曾经想要我搬去一起住,可是我坚决地摇头。战争不远,于是寒冷不远,三色坊满堂的牡丹独自在王国里绽放,无人问津。
扬州的春天,美丽可是凄凉。不断地有衣衫褴褛的难民涌入。他们来自不远方战马践踏下的城池。睁着灰白的眼睛,呆滞而茫然。我开始在店门口支起大锅,雇了逃荒而来的少年伙计,夜以继日地熬着自制的药粥。我把很苦的中药熬在一碗碗粥里,扬州薄瑾,于是成了众人口中那一朵浮世的莲花。我只是不治刀伤剑伤,那些来历不明的伤者从我眼前走过,脚步沉重。而我抬起头来看天,再一次记着祖父那两句没有缘由的承诺,像信奉一场自己亦不知原委的浩劫。
六月的扬州垂柳绝尘,我听到脚步匆匆的商贾口中的传言:唐公李渊次子遇伏,败,全军覆没,惟与副将突出重围,遭窦建德大军一路东下追杀。
刚好是我祖父死去的一周年,无数士兵的头颅在远方被砍下来,无数绝色的牡丹在我寂寞的手指下枯萎掉。我不停歇往锅中投入一味味中药。每一朵都是一个苦涩的故事,我梦想着这些药被喝下去,于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苦涩,而我的牡丹一朵一朵摇曳生姿,于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了禁锢。
乱世中的扬州春末,我轻轻抬首见到男子朝曦降落的脸。他背向烛火站着,有一双亮若星辰的眼睛。他的脚下横躺着另一个颀长挺拔的身躯,有我所熟悉的鲜血味从他身体的某个缺口决堤而出。男子朝曦居高临下地说,救他。面无表情可是言语间,草木皆兵。
我记起我的祖父,战争开始了他只有离去。我在他最钟爱的钟翠山下合上棺盖,泪水像蝴蝶一样迅速干涸在冰冷的琥珀。我说,对不起,我救不了他。
朝曦的眼神在一瞬间变得锋利,他的手搭上腰间那把苍黑的玄铁刀,凌乱的头发上有扬花的尸体,他冷笑,说,你都没有看他一眼,问一下他得了什么病,你算什么大夫,你给我站起来。他的手指压在我凛冽的肩胛上,于是骨头开始不安躁动。箭伤流血过多,只有九转膏能起死回生。我指向正堂的告示,而九转膏早已封存,先祖更明令刀箭不明伤不得医治。他的手在我肩头的力道渐渐加大,烙满灼烧的痕迹。至于站起来,我轻轻吸了口气,拂开盖至脚踝的裙摆。于是像童年无数个黑色的梦魇一样,我再一次看到自己如衰败的牡丹一样枯萎的双腿。在朝曦不知所措的目光里我说,扬州薄瑾,天生不能行走,望请见谅了。
我在虫鸣鸟语的深夜向陌生的男子打开我生命的缺口。韶华白发,最美的年华,连站立都是一种奢侈。血液就这样干涸了,十指生长出荒凉的曲线。
他的手在我的肩头缓缓松开,我躲开他一瞬间变得怜悯且复杂的眼神。然后在我眼泪掉下来的前一刻,深夜突兀闯进我房间的男子缓缓地蹲下来,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把我的裙子整理好,在迷离的烛火笑颜明媚若虹。他说,你绣的牡丹,很美。
我转过头见到从墙上撕下告示的朝曦。一字一句,他念了三遍。而在他还到我手里的那一绢牡丹里,我触到了一瞬间的鸿蒙温暖。这上面说的,算数吗。算数,我不假思索。朱红的烛台被他猛然抓在手里,那些火扶摇而上,呼啸的流金从他的衣袖一直猎猎烧到手臂。在一树桃红的呜咽中,北方男子的壮烈广袤无边。红烛最后一滴血在他手臂化开,他举着满目创痍的手到我面前,微笑,这不是刀箭伤,可以给药了吗?
男子朝曦用仅存的一只灵活的手从我手中接过九转膏,毫不迟疑地将膏药贴在地上男子的创伤处,鲜血立刻停止了溢动。他欣喜地看着我笑,脸上有孩子似的明媚:薄家神药,果然名不虚传。多谢小姐救命之恩,来日必当报答。
我用手势制止了他预备抱起地上男子离开的动作。将另一帖膏药覆盖上他的伤口。在他落到我脖子的头发里,我听见祖父长长的叹息。
扬州山雨欲来的满楼风里,我抚摩着朝曦开始结疤的手臂皱眉说,没想到伤口这么深。朝曦会拍拍我的头,他的笑是北方天空下才有的深远和温暖。他说就快好的,我的手贴上你的膏药一点都不疼了,一点都不。
我的祖父离去了,留我一个人生活在春色凋零的扬州。而我用他不愿再见天日的两帖膏药,留下了这个叫朝曦的北方男子。他有麦田一样明亮的微笑和温暖的手掌,在他的手落在我寂寞纠缠了十七年的长发时,我能够看见童年所有关于奔跑的梦想。蓝的天,白的云,嫣妃色的晚霞里我的裙子飞扬起来,带着少女特有的骄傲矜持,和无忧无虑。
大隋朝已经死去,天空中有巨大的弓箭阴影。王世充招兵买马已经称了王,瓦岗寨的烽火早燃烧了整片晚霞。窦建德的战马在大荒的天下伏地悲泣。而太原李家,那个始终沉默而神秘的家族又看见了蹁踺的凤凰。
而我长久地倚在自己半月形的窗台,听朝曦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北方那些遥远的城市。像我童年无数次的那个梦境一样,古老而繁华的长安洛阳,开满了艳丽的牡丹。朝曦说他的家在那里。他对我说,薄瑾,你是适合生活在北方的,在紫塞消瘦的白草中,你骑上那些高大漂亮的马,头发和裙子在空中打开一个一个漂亮的圆弧。你的耳边只剩下了飞翔,和,无边的欢乐。他心疼的看者我一直没有生命的腿,用温暖的手轻轻覆在我的膝盖,然后问我薄瑾你会不会冷。我微笑着摇头,说,不会。
那个被朝曦抱来求医的年轻人身体已经飞快地复原了。我从未见到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以拔节的力量冲破了整个阴霾。朝曦叫他大哥,表情专注而且尊敬。我在清晨的曦光里看见他站立在我一屋子悬挂的牡丹织锦中。和那些绝尘的花中之王连为一体。我听见林中野兽蠢蠢欲动,那些滚滚而落的烟波和走到涅磐的太阳河臣服的呐喊。
也是在那芬芳的一屋牡丹中,朝曦把半面有着参差不齐伤痕的玉佩交给我,还带着他残存的体温。他温暖的手掌摩挲着我的脸颊,薄瑾,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北方吗?那些翩若惊鸿的鸟,给你安上翅膀的风,和我希望给你的,永远飞翔的自由。毫不犹豫,我说,我愿意。
千江水,千帆落,暮野沉沉楚天阔。地披赤水衣,天是红河岸。朝曦的大哥忽然唱起这样一首奇怪的歌。他看者远方不见尽头的落日。说,我该回家了,那里,有我的家人,兄弟姐妹,和,东土九州留给我的使命。
垂丫少女抬首采下一串槐花,她们清澈而悲伤地唱:扬花落,李花开,盛世红墙自北来。
扬花落,李花开,一曲未完,我便目睹了这个大荒的晚春,扬州最无妄的一场浩劫。那些冷漠的马,铁蹄高高扬起,踏着满地的槐花尸体,落在少女光洁的小腹。街上的人们仓皇奔走,下意识重复了那些待捕的野兽绝望的喊叫。慌乱的尽头,是整装的战士,冰冷的刀剑,和,迎风展开的“窦”字大旗。
门口用来支粥的大锅被慌乱的人群撞翻,那些乌黑的药汁,是一滴滴苦涩的眼泪,屈辱最终汇成大海汪洋。朝曦的眼睛中出现张皇和犹豫。而他的大哥,缓缓抬起头来。一瞬间整个视野,残阳如血。
为首的将军站在九味堂的大厅,目光锋利。他警觉地看着我,问,有没有一个胸口受重创的男子和他的属下来这里求医。哦,他的唇齿间有十二月的冰雪,而我看到的是我的北方之北,白色的阳光,朝曦那凌乱散开的头发和我飞扬的裙角。我于是微笑,对不起,没有。而且,我再一次指向那被朝曦撕下我复又贴上去的告示,将军应该可以看到,先祖早有遗训,小女不敢有违。在那遥远的钟翠山,我的祖父,亡灵居住在最茂密的一片森林。他的目光落在我的眼角,是谁的叹息喷涌而出,点开一树银花。
封城,扬州,饥饿和鲜血交互辉映。城池是溺水的孤岛,四野楚歌海天阔。
我是这样敏感和聪慧的女子,所以在窦军破门而入前我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是及时打开了祖父用来储藏珍贵药材的那个暗仓。送走窦军将领,我微微弯身:李二公子,你好。
唐公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对我辨别出他的身份并不感到惊讶。或许我们早已心照不宣。朝曦的眼神先是惊诧,继而感激,然后,是我所熟悉的怜爱。他忽然紧紧地抱住我,手指因为太过用力,凸露的骨节在我的肩上像是突然绽放的焰火灼热。接着,他飞快地转身,说,走吧。
燕娘在日落时分面西而立,她的衣裙如同云朵一样温柔地芬飞。她沉默不语,看着我和朝曦,眼神鸿蒙迷茫。晚春,天凉似水,花谢如茕,我用一只鸽子唤来我城西的师傅燕娘在朝曦身边,并且告诉她,这是薄瑾,誓死也要保全的人。于是我再一次见到了燕娘那变得奇特的眼神。在某个遥远的春天,她这样低下头,然后我的祖父死了,她湖蓝的衣袖上血红的牡丹娇艳欲滴。
许多年后依然有人记得扬州那场百年难遇的大火,天空被烧成了赤焰色,所有扬花的容颜悲伤垂落。朝曦将那块布满参差伤痕的玉佩挂在我的脖子上。这是我未曾谋面的母亲留给我的,他说等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在扬州城外的钟翠山上等着你,我会一直等着你。那一瞬间我见到我的师傅,眼波里氤氲的雾气。她带着朝曦和李世民一直消弭到那些火光嫣然的尽头。而天地如墨,如此沉沦忧伤。
我扔掉手里的烛台,沉重的铁甲摩擦声在南方的天空上持续轰鸣。我知道那些凌厉的士兵全部涌向了这里,从扬州的各个角落。我对祖父说,我要让所有的一切有个快乐的结束,然后天高云淡,万物清澈如初。那些牡丹的亡魂流出青涩的血液。她们告诉我说,他已经走了,在扬州空无一人的西城。
九味堂就这样付之一炬,浓郁的药香夹杂着一阵阵的焦热长久地环绕在半空。为了引开窦军的注意力,祖父的全部家业化做了淡薄的青烟。
窦家的兵马搜遍了所有的废墟残骸。而我一言不发,在牡丹流水的颤栗里,像个最单纯的孩子一样演绎着悲伤。可是我闭上眼睛居然再也没有看到过朝曦,在那不知名的远方是突兀横卧的一条江,江畔大雾茫茫,我一直往前找寻居然就看到了燕娘,手指一片绯红的鲜血,
扬州大火的第四天,窦军开城撤退。他们掘地三尺,无功而返。于是扬州一战,为太原李家再添了一份神秘的气息。而二公子李世民,终于在传奇的渲染中喷薄而出,从此长盛不衰。
鲜血远去,战争远去。而爱情无期,风月有尽时。
我长久地张望扬州自西而来的古道,日复一日重复等待。而城门紧琐,良人不见归期。钟翠山上一片荒芜,连同我的师傅燕娘,从此消失了踪影。
我去过城西的三色坊,年迈的老管家问,小姐,你是送织锦来的吗。时逢乱世,没有主顾啊。我摇头,我只是来看看。他不知道,我再也绣不出牡丹了,我那些绣牡丹巧夺天工的技艺,在那场大火后便莫名地消失殆尽。所有的一切,随着朝曦的离去,在火花的魅影里荡然无存。只余我一人垂一头岁月的苍凉,一边缅怀,一边感伤,一面沉沦,一面落寞。
曾经朝曦对我说,你是适合生活在北方的。后来他不见了,我的血从紧咬的唇中落下来,盛开扬州一夜春秋。
我的祖父在天的尽头缓缓出现了,他充满怜爱地来抚摩我的脸。孩子,对不起,我以为一切的一切,随着我的离去可以终止。而天无涯地无尽,轮回生生不息,最后还是把你推入旋涡。
朝曦和燕娘了无音讯后我最亲近的人是三色坊的老管家李成。我们在九味堂沉寂的废墟中找出那伤痕明灭的半块玉佩。然后我不厌其烦对他讲到我周而复始的梦,祖父悲伤而疲惫的脸。于是终于有一天,白发苍苍的老管家李成抬起浑浊的眼睛,他说我终于明白天地万物循环不息,一切是没有终止的。所有的悲伤,仇恨,鲜血,只不过在无尽的时空里流转,在适当的时期再带来新一轮的悲剧。那么好吧,是让你知道一切的时候了。
朝曦离去很久的夜晚,扬州百花凋残,所有尘封的故事在这里打开。
是十八年前一个叫薄与生的浪子,抱者嗷嗷待哺的孙女。他一直都在行走,从边塞的白草到扬州的烟花六月。怀中婴儿的嘴唇由于饥饿和颠沛长出青色的水疱。他停了下来,决定再也不往前走一步。
他停在李园门外。
李园的女主人燕然有一张娇柔明亮的脸,少年时爱慕的郎君跨上那匹高大英俊的马。他说战争结束了,我就回来和你阳春三月,共放纸鸢。而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所以他再也没有回来。于是燕然常常保持的姿势是坐在窗边,在一匹匹展开的巨大织锦上绣那些华美的牡丹。只是这一晚,她手指下永远盛放的牡丹突然死去。忠实的管家李成抱着啼声已渐行渐殇的婴儿站在烛火的阴影里。他说,夫人,少爷怕是,不行了。然后泪流满面。
李园正堂灯火璀璨,北方的游子指间夹着家传的银针。他小心地拂平刚刚睡去的孙女眼角最后一滴惊恐,然后细细地审视整个屋子。燕然的脸焦灼而忐忑,她说请先生救治我的孩子,任何代价在所不惜。我年轻的祖父于是抬起他消瘦的脸。他说,给我你的房子,我治好他。
昔日李园的管家李成老泪纵横,小姐你看这付之一炬的九味堂,十八年前它是扬州最繁华的宅第,风香鸟语,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水人家饶。李园女主人燕然的牡丹织锦洛阳绝色,天下无双。而如今,兴败荣辱,俱是灰尘,你看到了吗。
还是个孩子的我午夜梦回,梦里我是生长在北方的女子。那些来往穿梭的胡商,那样高远广袤的阳光,无边的草原上我放肆奔跑。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我的双腿在一夜突然死去,神医薄与生也束手无策,所有的奔跑只能出现在遥远的梦境。远方大运河上有我的血脉在哭泣。面容模糊的女子嘴角咬出血来,她说,报应。
一夜之间,扬州最繁华的宅第李园变成了药馆“九味堂”。而那个被人乐于传道的女子燕然,从此踪迹全无,就如同大隋王朝迤卷在天空的扬花,一飘落,就再也找不到归途。
再次见到燕然是十五年前扬州街道上,她沉静地站在一堂的织锦中,三色坊的牡丹盛开如血液。昔日高贵的妇人燕然化身扬州最神秘的织女燕娘。她倚门而立,挽起的头发翩若惊鸿。说,管家,我回来了。
她只是缄口不提她的孩子,那个被我年轻的祖父改变一生命运的孩子。而我看见了燕然抓着婴儿空荡荡的包裹,在战争过后的土地上奔跑,问每一个茫然的灵魂,有没有看见我的儿子,你们有没有看见。他们把她团团围在中间,木然地说,他一定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我抬头看燕娘的脸,十五年后的燕娘有一双和少妇燕然一样深邃的眼睛。而我,祖父,薄家,终于如她所愿,一无所有。
所有的人终究都还是回到了这里。
我那把我独自留在江南的爱人朝曦,他看着我,用他那清澈而莫名的表情,终于回到已经埋葬一切的九味堂。他一只手扶着燕娘,一只手握着那把苍黑的玄铁刀。芳草戚戚,没有人问,薄瑾,你冷不冷。他低着自己的头。
燕娘说,薄瑾,你看到了吗,那是我死去的家园。烧成平地的九味堂胸前有一个撕裂的伤口,哭泣如斯幽切。眼前一片鸿蒙,我问低着头不再给我任何关于北方畅想的男子。为什么,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回来,诀别吗。
我的掌心像茫茫的雪海一样寒香弥漫,在他抛下我跨上北方的战马后,在他扶着燕娘如去时一样突兀地来到我的面前之后。所有的温存和流光,终于纷然消失。
往事音书全部变化成我所不能控制的样子,燕娘抬起头微笑的样子像个高傲的女巫。我好像再难以把她和那个在童年用华丽的锦缎给我一个美丽的梦的师傅联系起来。可是为什么,祖父,朝曦,所有的人都愿意就这样莫名地,喝下她眼里的毒。
所以,我抚摩着温润的玉痕抬头看朝曦的眼睛,对他微笑,我说朝曦,这块玉佩,是一个答应一直要等我的人送给我的,现在他在哪里。他的脸孔突然变得痛苦,他说,薄瑾,然后再也发不出一个字,声音溺死在日暮的水底。我微微地点头,然后用尽了拔节的力量从朱漆的椅子上,滚落。朝曦慌张地跑过来,在他沉重而惊恐的表情尽头,我把他腰间的那把玄铁刀深深刺进了他的心脏,那些飞舞的血花染上我的雪白衣衫。于是一瞬间,我见到他模糊而温柔的表情。他说,薄瑾,我终于回到你的身边了,再也不会分开。
潺潺的血液茫然流淌,燕娘撕心裂肺的尖叫起来。她骄傲的神情突然崩塌,青色的泪水开满整个脸颊。她抬手,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重复了许多年前的那个战后,她野兽一样的哭泣。她奔跑,问每一个亡灵,有没有看见我的儿子,你们有没有看见他。然后所有人都说,他一定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我握住燕娘衣袖中坠落的半块玉佩,带着参差不齐的伤痕,和一个轮回的诅咒叹息,在朝曦尸体上还温热的血河中,和朝曦留给我的玉佩合为一体,再也,不能分开。
流转的往事前尘如散落的扬花扑面而来。钟翠山上,燕娘的眼睛显露出从未有过的温情。她颤抖着手摘下脖子上垂挂了一十八年的半块玉佩,伤痕华美。独自在北方长大的流浪儿朝曦忽然泪流满面。她叫他,孩子。于是我的脸被那些陌生的仇恨浸染得陌生而模糊。他低下头,扬州所有的记忆是幻灭的一场流光,绝尘而去。
恍然间,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祖父。孩子,我们回家吧,回家吧。
我看着血泊中朝曦安静而释然的脸,说,好。
许多年以后,大唐盛世,贞观之治。英武的太宗经过长安郊外。他在朝南的高岗上见到了安静的白衣女子。
北方广袤的大地上,面容平和的太宗骑在高达漂亮的马上。他坚定而略带悲伤地对我说,我带你回家吧,朝曦他已经死了。
塞外的风穿过长安高远的阳光,我的长发和裙子飘样起来身体只剩下了飞翔,和无穷无尽的自由,像朝曦无数次给我的那个关于北方的真实的梦。
在太宗诧异的表情中我抬头微笑: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一起,并且,再也不分开。
在山岗的最高处,面向扬州的方向,我的师傅燕娘发白如雪,她旋转,起舞,妩媚的容颜是绝世的姚黄魏紫。她小心地抚摸着我迎接了每个冰凉日落的脸庞。笑,我是扬州李园地主人,少爷朝曦的娘亲。我的名字,是燕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