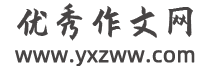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人,大概都会觉得惠州的冬天没什么意思:春天没意思,夏天没意思,秋天没意思,冬天可就特别没意思了。叶不落,花不凋,望不见那白雪皑皑的山,看不到那冰冷清凝的河冰。只有那净寒的风夹着一点不合时宜的细雨,零零落落的打在街上,湿漉漉的,却也成不了气候。待到惠州的风和这北方的雨起哄,才顺势冷它几天。可毛衣还没穿几次,围巾还没戴几天,却有道,春分来了。惠州人说,那冬天是糟蹋了自己,也糟蹋了春天,瞧不见那截然不同的变,便也没有了去留意的心思。
北方人都羡慕惠州冬天的暖,临行的时候披一件潇洒的外套,便可充当御寒了。路上还有葱郁的树,不像北方,净是光秃秃的树枝,让人看了可怜。而惠州人又盼望着人家北方的雪,咋一看,这楼顶楼面全是雪。远看,一片茫然;再远看,还是一片茫然。可惠州人说,那是干净,那是气势。但你如从北方带回惠州的柿子,惠州人初一吃,是要大赞特赞的,说什么不像惠州水柿那样,净是水,也没有什么肉感,而且还不怎么甜。可是,带到这千里遥遥被运回来的柿子被放得破了皮,发了霉,那才知道想着的还是水柿。对惠州人来说,那带着雪的北方的冬,那棉袄,那皮帽,那刺骨的风,那冻人的雪,兴许只能远观而不能玩的了,
惠州的冬天向西方借来了一个圣诞,那样人们就有借口把那些不冷的“雪花”洒在各自的窗台,而不至于遭北方人的笑话。从这样的窗子朝外望去,却也是一片朦胧,直真似那北方窗台上真正的雪。人们在脖子上围一条可爱的围巾,轻轻地哈着气看着那稀薄的气体从口里散到空中,,然后静静的说一句:这个圣诞可真是"冷“啊。这边也仿佛有了冬天的味道。
橘生淮南而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惠州的冬天诺是在北方播了种,也许就不是这个冬了。如此看来,我们的冬天还是值得好好收着,藏着,尽管它暖,尽管它润,可在北方,它却是个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