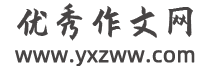刚下过小雨,天仍未彻底放晴。地是湿的,嵌在泥土里的石头被雨水冲刷过,凸显出它们的坚硬异常,让这条本就泥泞的路看起来更加坎坷、崎岖了。
最后,爷爷在这条路上蹒跚地走过,走向那垂暮的夕阳。他走着,未曾回头望一眼这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
自我出生起,爷爷就从湖南就来到了广州生活。
记得小时候,我上幼儿园是要坐一段公交车的,车站离家并不远,但出了家门后,爷爷总会让我牵着他的手。坦白说,牵着爷爷的手并不舒服,皆因那满是褶皱的手实在是太有力,有时甚至握得我有些吃痛,手掌上布满的茧子更是常常磨着我的手心。但走在爷爷身后的我,却始终不敢松手。爷爷的步子迈得大而快,倘若我一松手,恐怕立刻就会因为失去重心而跌倒罢,我想。突然,一辆车从身旁的马路上呼啸而过,爷爷又紧了紧他的手,转头看了看那车,我呢,我看着爷爷。他宽厚的身躯,挡在了车来的方向,与灰白的头发并不那么匹配的直挺挺的腰板,是从未弯过的。
走到车站的站牌后边,爷爷操着一口乡音教我认字,他仍牵着我的手。空旷的马路上吹来的风小了些,我牵着爷爷的那只手也出了汗。
就这样,爷爷牵着我的手,走过了许久。
六岁那年,爷爷查出了肺癌,晚期。手术后,癌细胞转移,化疗的效果甚微。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是知道爷爷的精神没有从前好了,身体没有从前好了。
一天中午,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爷爷没来,我便去叫他。爷爷坐在房间里那张老藤椅上,眯着眼,似乎是在打着瞌睡。“爷爷,吃饭了。”我走近爷爷,大声地说。爷爷睁开了他浑浊的眼睛,缩了缩身子,紧接着便是一阵急促而用力的咳嗽,使藤椅嘎吱嘎吱地摇了起来。“没事吧,爷爷?”我有些被吓到,连忙问道。爷爷摆了摆手,似乎是艰难而缓慢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摸了摸我的后脑勺:“没事,你先去吃吧。”说罢,似乎是用力挺直佝偻的身子,又摆摆手让我先出去。“等一下,”他又叫住我,“有辣椒吗?”
我出去了,坐上桌,那餐饭并没有辣椒。我几口扒完了饭碗里的饭,爷爷却没有出来,下午,爷爷进了医院。那天晚上,爷爷走了。
带着爷爷的骨灰,我跟随父亲回到了故乡。湖堤上,父亲把车停了下来,指了指湖边的几栋小房子。他告诉我,爷爷把老房子卖了,原本想要在这里买房,可是因为要照顾我,爷爷最终还是没有买。我后来又知道,那里住着的都是爷爷的老战友们,爷爷很想他们,也跟父母提过很多次。爷爷十八岁从家里出来,到邻市参加工作,生活在那里,退休后又来到千里之外的广州。现在想想,确算是个背井离乡的人,他和我们一起生活,却从没有说过想家,也从没有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爷爷他太坚强,甚至都来不及脆弱,来不及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