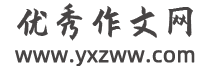生活必然是这样的,有波澜不惊,也有阴霾骤起。一个窘迫的男人,一个卑微的务工者,在坚硬粗糙的岁月里,没有惊惧地尖叫着跌下去,碎成一地绝望的粉末,而是选择在疼痛里开花,开一路温暖的黄花,笑着或歌着,走过那些或平坦或崎岖的路。
每一次遇见他,都是偶然,许多个偶然的一瞥,竟也串联成一个完整的他。我不得不惊异于命运的巧合,原来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陌生人。
第一次看见他,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个拉煤球的,成天蹬个三轮车,一身的煤灰,脸上、身上也都是黑兮兮的,一顶总习惯歪戴的棉帽子和总不习惯系拢的外套是他雷打不动的造型。他似乎生来就那么瘦小,一张脸真正是棱角分明。却凭着这样一副小身板,他每天清晨总是很及时地蹬着装满煤球的三轮车,哼着不着调的老歌,穿行在大街小巷里。许多时候,顾客总拿他开刷说“小伙子,什么时候娶媳妇啊?”“明天,明天就娶”他爽朗的应着。又蹬上车子,唱着老单身汉的情歌,挨家挨户的送煤。
一连几年,我和他总在清晨的时候,骑着车擦身而过。没有过多的言语,连例行的招呼都被省略。碰上下雨天,路窄不好走,他会很耐心的停下车,尽量地靠近内侧,然后沉默地一招手,让我们先过。目的就是不想让其他人碰到脏兮兮的煤灰。更多的时候,是我静静地欣赏他的老歌,近了,又远了。
毕业后,我再没有走过那条路,也就渐渐地淡忘了他。直到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夜市上又看到了他。他依然瘦小,罩着一件很肥大的背心,露出不很健壮的古铜色的手臂,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很老气的女人,腆着大肚子,大胳膊大脚,谈不上漂亮。男人很满足地拉着女人的手,另一只手里,提着许多家庭生活用品。现在,他终于告别了那些单身情歌,总算有了一个家。我想象着,累了一天的他,回到他们的那个小家,看着女人张罗的热腾腾的饭菜,傻乎乎地乐着。
这几年,我去学校的垃圾箱倒垃圾时经常能碰到他。他已转行成了一名环卫工人。他还是他,那么瘦小,一双半新不旧的解放鞋,套着环卫工人的红色马甲。那辆三轮车也比以往的拉煤车气派,更衬出他的瘦弱。他一铲子一铲子地往车里装垃圾,很卖力。三轮车前面的大车篮里,通常坐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吸着鼻涕,晒得黑黝黝的竟毫不怯生,男人铲累了,点一根烟,对着儿子,呵呵的乐着。当有人来到垃圾时,他总很主动地迎上来,接过垃圾桶,倒入垃圾箱或直接倒入车里,细心地拍拍,再叮咛一声“下次早些来”
装好后,拍拍儿子的头,吆喝一声,蹬着车,威风地离去。
生命就像一个瓶子,被填充的内容就构成了生命的质量。这个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在短短数年间,从单身汉子到丈夫再到父亲,男人肩头的负担愈发重了,然而他的生活品质并没有多大起色,他依然蜷缩在城市高楼大厦的阴影里;儿子、妻子,这些都是需要用一生来承受的重量。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压垮他那颗乐观的心。尽管,负担仍会膨胀,但是这个瘦小的男人,依然哼着小调,用心磨砺着生活。笑着或歌着,走过那些或平坦或崎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