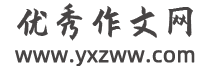爷爷离开我已两年了。他的音容相貌被时光偷走,于是我只记得他的影。
大概是三年前,爷爷刚切除完肿瘤。他腿上的一部分肉被拿去填补肿瘤的空缺,整个人显得如此不堪。他的大腿似没有肉色,刀曾经无情地插入那些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沧桑的肉,冰凉紧贴疼痛。我无法想象。
一次饭后,爷爷硬拉着我去散步。我极不情愿地离开电脑,趿拉着一双拖鞋出了门,只想着快去快回。那时爷爷便跟着我边小声嘀咕些什么,焦躁的我听不清。那些喃语现在无限清晰地回落在我耳边:“也没几次能陪你散步了。”
我在前方走,爷爷在不远处追。我一刻也不愿等,非常不情愿地放慢脚步候着爷爷。他气喘吁吁地追上我,说:“在那休息一下吧。”只有一层皮的手指颤抖地伸出,指向路边长椅。我看着他瘦削却高大的身躯,便在路边坐下。他全身松软地靠在椅背上,无力地仰着头。逐渐暗沉的天,如一团重墨倒在水中,逐渐浑浊的过程。我看腻了光怪陆离的城市,扫视着周围。视线停留在爷爷的足部,再也移不开。我忘了,忘记了肿瘤长在他的足部。不过,那儿如今只有一块肉,周围是密密麻麻的线。我的心像被什么给狠狠揉得变了形,只呆呆看着那处不看,一动不动。
走吧。”爷爷忽然开了口。我扯着他的衣袖:“可以再休息一下的。”他像是读懂了我的顾虑,怜爱地笑着拍拍我的头,站起身。路灯已然亮了起来,一高一矮的影子在砖上斑驳。不知为什么,爷爷的影子特别瘦削。那抹黑色轻微的左右摇晃,衬得灯光十分晕暖。我忽而忆起幼时的自己牵着爷爷的受走过无数大街小巷,美好的回忆如潮汐般涌来,暖暖的。我紧紧抓住那双布满老茧的宽厚大掌,粗糙如它,岁月掠过的同时留下了细纹。爷爷摸了摸我的头,微笑着。影子紧密相依,透出亲情的味。
再注意到爷爷的影,是他被推往焚尸炉的前一秒。彼时他已不会动了。阳光从天窗撒下,爷爷躺在自己的影子上。我便想,他们都是曾经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与我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火放纵地呼啸着,我却听不见。那一刻是寂静的。仿佛一座钟往心敲去,一种情绪由内而外,震荡了全身。
爷爷与影终化为灰。
在他的忌日,我会独自一人斟两杯酒,想象他摸我的头,而我俩的影紧密相依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