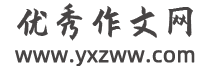“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年糕。大姑子,小舅子,远亲总比近邻好……”古老的儿歌在空气中来回地飘荡,倒映出无数轮回。石碑静默地立在村头看着几百年沧海桑田,而歌声依旧。
三百年前,县官接到快马来报,滁州境内瘟疫泛滥,凡染病者半月之内咳血而死。县官立即下令全县戒严,不许任何来自滁州者入内。
三百年后,村西的黄四娘接到儿子电话,说是在北京染了肺病,准备回村调养。
历史的轨道以平行姿态延伸,前后追逐着;历史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苏醒,今昔审视着。
县官坐卧不安,自己膝下无子,只有在滁州城北的弟弟一家亲戚。倘若他们来县里避瘟疫,要不要开城门呢?
黄四娘心里咯噔一下,忙问儿子是不是得了报纸上说的那个传染病。儿子在电话那头咳了两声就挂了。
几天后,县官走向了城门,黄四娘走向了村口。历史的轨道也紧密地切合在一起。
“伯父,我爹娘都染病死了,全家上下就剩我一个了。我拼了死才逃到您这儿来的。伯父,您开开城门吧。您不能见死不救啊!”门那边县官的侄子哭着。
“妈,我回来了。”村外边儿子向着黄四娘走来。
历史带着厚重的颜色重合在一起,沿着时间的墙流淌开来。
门这边县官老泪纵横:“我已下了禁令,我得对全县百姓负责啊。”
村这头黄四娘后退了几步:“儿子,听妈说句话,别往村里走。”村民们渐渐围上来,在黄四娘身后围成一个半圆。
“伯父,您开开城门吧!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要死也得死在亲人身边哪!”
“妈,你让我进村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要死也不能死在外头哪!”
理智与情感分别立于天平的两端,亘古的风吹过,历史在继续。
门这边县官不断地踱着步,作着他这一生最大的抉择,理智与情感的天平逐渐倾斜,县官最终在夕阳西下时下令打开城门。村这头黄四娘流着泪从村民手中接过了扫把:“儿子,今天不是妈狠心,但只要妈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让你进村。你看看妈身边这些乡亲,他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忍心把病传给他们吗?你还记得这村头石碑上刻的字吗?理智点吧———你是妈的儿子,可妈不能因为你而害了全村人哪!———你得照电视上说的做啊!妈已经打电话给了防疫局,他们马上就到了。”
历史的轨道按照它熟悉的方式重合在一起,却最终折向两个方向。
石碑上刻着:嘉庆七年,滁州瘟疫泛滥,本县县官内侄自滁州来县,县官开城迎侄,数月之内,全县死绝。
亘古的风带着古老的气息拂过石碑上模糊的字迹,沿着时间的轨迹讲述着一个关于理智与情感的久远的故事。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年糕。大姑子,小舅子,远亲总比近邻好……”古老的儿歌在空气中来回地飘荡,倒映出无数轮回。石碑静默地立在村头听着几百年歌声依旧,只是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